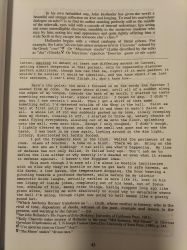
第五章(续)
约翰·霍兰德以他独特的、令人困惑的方式,为世人呈现了关于爱与渴望的美丽而奇异的思索。阅读他那关于回声的奇妙对话,就如同看到作者站在人行道上,双眼带着一连串内心的盘算,嘴唇吐出一些难以理解的话语,这些话对众多匆匆而过的学生来说听不见,而学生们则明智地与他保持距离,逃进别人的课堂。
例如,霍兰德以一份几乎是字面回声的目录开篇。西塞罗所说的“decem iam annos aetatem trivi”(十年的青春时光)在希腊语中回响为“one!”(一!),或者“Muses' study”(缪斯的研习)在拉丁语中被描述为“Lunior, quam sit tibi copia”(年轻人,愿你拥有丰富的资源)。
*我盯着文字,想要找出至少一处不同的重音或字母,在这个追求中几乎变得绝望,却只是反复发现它们完美的相似之处,尽管这怎么可能呢,对吧?如果它们是完美的相似,那不就意味着它们是相同的吗?你知道吗?我迷失在这句话里了,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结尾——
就在这时,我闻到了味道,那是我父亲房间里传来的味道。一开始我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,直到突然之间,沿着我的舌尖边缘,向口腔后部蔓延,我尝到了极其苦涩、几乎像金属般的味道。我开始作呕。我试图忍住,但我确定自己会吐。接着我又闻到了同样的味道。那味道糟透了。我在外面的走廊里发现了它。一开始很淡,淡得要命,直到我意识到它是什么,然后它就不再淡了。
一整堆腐烂的东西突然涌入我的鼻腔,慢慢地顺着我的喉咙向下蔓延,越来越浓。我开始呕吐,水汪汪的呕吐物溅到地板上,溅到墙上,甚至溅到我身上。除了咳嗽,我什么也做不了。我轻轻地清了清嗓子,然后我闻到的味道消失了。我不再尝到那种味道。我又回到了房间里,在昏暗的灯光下四处张望,心神不宁,几乎被愚弄了。
我把碎片放回箱子里。在房间里走了一圈。端起一杯波旁威士忌。一饮而尽。来吧。让这股雾气弥漫开来。但我在骗谁呢?我仍然能看到发生了什么。我的防线早已崩溃,很久之前就崩溃了。别问我为什么防线会崩溃,也别问我为什么现在需要它来抵御这些。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拿这团雾气怎么办。
我不太确定,但我感觉自己好像置身于敌境,不知道它们为什么充满敌意,也不知道怎么回到安全的地方,就像一个迷失在茫茫大海中的老水手,气温骤降,向着深邃的黑暗倾斜,而我之前那些愚蠢的、自鸣得意的笑声,现在听起来更像是一个迷失在自己的一连串内部笑话中的白痴,完全脱离现实,心不在焉,注意力不集中,就像齐恩琴弦一样,很久以前就断掉了,让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,尽管现在似乎地狱是个不错的归宿。
51 安东尼·邦纳将其翻译为“……真相,其主人是历史,历史是时间的对手,是行为的宝库,是过去的见证,是现在的范例和对未来的警示。”—— 编者注
52 见约翰·霍兰德的《回声之图》(伯克利: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,1981 年)。
53 凯莉·查莫托在她的文章《句中,流中》中提到了霍兰德,该文收录于《光荣的闲聊书法》,T. N. 约瑟夫·特鲁斯洛编(爱荷华市:爱荷华大学出版社,1989 年),第 345 页。
“我在西塞罗身上花了十年时间。”“蠢货!”
“缪斯的研习”“神圣的事物” 。
